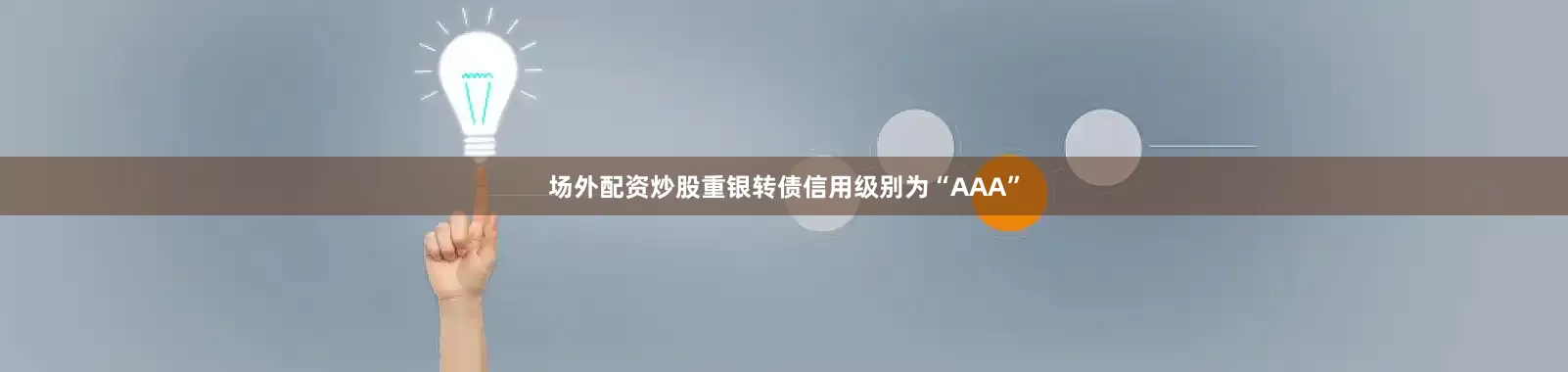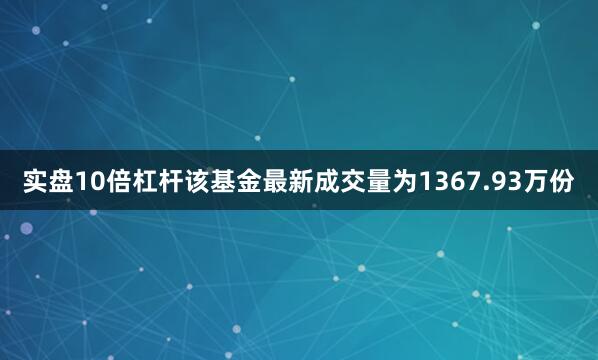《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及目录六十卷。

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依韵分列单字,又在每一单字下注明音义、反切及篆、隶、楷、草各种字体等,然后将有关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人事、名物等材料,随字收录。所收材料中,有整段或整篇抄录的,也有整部抄录的。其中收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达七、八千种。
在《永乐大典》“戏”字韵下,即卷一三九六五——一三九九一,载有戏文三十三种。后因兵灾人祸,《永乐大典》的正本在明亡之际就已失传,副本先后经历了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两次侵占北京的浩劫,或毁于战火,或被劫往国外,几乎丧失殆尽,今存仅三百七十余册,而“戏”字韵下所收录的三十三本戏文也已失传。
1920年叶恭绰先生在英国伦敦一小古玩肆发现了《永乐大典》收录戏文的最后一卷,即第13991卷,戏文廿七,收录的《张协状元》、《错立身》、《小孙屠》等三种戏文,便将其买下并带回国,这是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
1931年,北京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据钞本刊印,题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原件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

《张协状元》,原本未题作者名,但据副末开场及第二出的【烛影摇红】曲所云,当是由温州九山书会才人所作;又曲白中多有温州的方言俗语,也可证明此剧为温州籍作家所作。
关于《张协状元》的产生年代,从其文本形态、故事内容及剧本中所保留的诸宫调、大曲、唱赚、宋杂剧等两宋时期的表演技艺来看,当是两宋时期南戏早期的作品。
《宦门子弟错立身》,简称《错立身》,原题“古杭才人新编”,可见作者是杭州的书会才人。
《错立身》在元代也有同名杂剧,《录鬼簿》卷上在李直夫名下列有《错立身》一目。又赵敬夫名下也列有《错立身》一目,但注明“次本”,不是原作。李直夫,本姓蒲察,人称蒲察李五。女真族人。居住在德兴府(今河北怀来县)。生平事迹不详,一说官至湖南肃政廉访使。
贾仲明为他所作的吊词云:“蒲察李五大金族,《邓伯道》,《夕阳楼》,《劝丈夫》。《虎头牌》,《错立身》,《怕媳妇》。谏庄公颖考叔,俏郎君,谎郎君各自乘除。淹蓝桥尾生子,教天乐黄念奴,是德兴秀气直夫。”

李直夫现存《虎头牌》杂剧,写金朝军官银住马,因醉酒误军机,受到担任元帅之职的侄子的责打,事后元帅又亲自向他谢罪。在剧中反映了一些女真族的风俗,而且还用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曲调。
《错立身》也是写金朝的故事,完延寿马是女真族人,其父担任的是金朝西京河南府同知之职。
显然,《错立身》的原作者,当是出身女真族的北曲杂剧作家李直夫,而南戏《错立身》即是根据李直夫所作的北曲杂剧改编的。而且两者的“题目正名”也相同,如据《录鬼簿》所载,李直夫的《错立身》杂剧的“题目正名”作:“戾家行院学踏爨,宦门子弟错立身。”南戏《错立身》的“题目”作:“冲州撞府妆旦色,走南投北俏郎君。戾家行院学踏爨,宦门子弟错立身。”
两者后两句完全相同,显然,后者是承袭前者而来的。又在脚色体制、人物形象、情节与曲调的安排、语言风格等方面,也确实与杂剧有着渊源关系。
《小孙屠》,原题“古杭书会编撰”,可见其作者也是杭州的书会才人。《小孙屠》与《错立身》一样,也是根据同名杂剧改编的。

《录鬼簿》在萧德祥名下载有《小孙屠》一目,又《录鬼簿续编》在“诸公传奇失载名氏”一栏下也列有《小孙屠》一目,题目正名作:“清官长智勘荒淫妇,犯押狱盆吊小孙屠。”
那么在这两者中,哪一本是原作呢?我们认为,无名氏的《小孙屠》是原本,萧德祥的《小孙屠》是据无名氏所作的北曲杂剧改编而成的南戏,而且就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的《小孙屠》。
据《录鬼簿》所载,萧德祥,名天瑞,号复斋,杭州人,以医为业。《录鬼簿》谓其“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等。”贾仲明的吊词云:“武林书会展雄才,医业传家号复斋,戏文南曲衠方脉。共传奇,乐府谐。治安时,何地无才?人间著,《鬼簿》载,共弄玉同上春台。”
据此可见,萧德祥是武林书会中的才人,武林是杭州的旧称,故“武林书会”也可以称作“古杭书会”,而南戏《小孙屠》卷首原题:“古杭书会编撰。”因此,此剧就是萧德祥所作。
而且,《录鬼簿》谓其“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便是指将前人所作的北曲杂剧改编为南曲戏文,这里所谓的“古文”,当指前人所作的杂剧剧本。

又据清曹楝亭刊本《录鬼簿》在萧德祥名下, 还有《四春园》《王翛然断杀狗劝夫》《四大王歌舞丽春园》《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等剧目,虽也未注明是杂剧还是南戏,但既然钟嗣成在介绍他的生平时,谓其所作的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贾仲明也说他“戏文南曲衠方脉”,那么这些剧目也应该与其名下的《小孙屠》一样,也是根据前人所作的北曲杂剧,即“古文”改编而成的南曲戏文。
另外,从南戏《小孙屠》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脚色体制、场次安排、语言风格等来看,也确实能够看出其从元杂剧改编过来的痕迹。
本编据《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所收的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刊印本予以收录,原本不分出,也无出目,今据钱南扬先生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分出。
又原本顺序首为《小孙屠》,其次为《张协状元》,最后为《错立身》,今也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作了调整。

《荆钗记》,明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载录,不题作者名,清高奕《新传奇品》、黄文旸《曲海目》及姚燮《今乐考证》则皆题“柯丹邱作”。
王国维《曲录》谓“旧本当题丹邱先生”,“丹邱先生为宁献王道号”,故柯丹邱即明宁献王朱权。《南词叙录》已将《荆钗记》载入“宋元旧篇”,又清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也称《荆钗记》为“元传奇”,故其作者必为宋元时人。
清张大复《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王十朋荆钗记》剧目下注云:“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著。”吴门,即苏州古称。据此,《荆钗记》的作者柯丹邱应是宋元时期苏州敬先书会中的书会才人。
《荆钗记》虽为宋元时人所作,但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改编,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如《南曲九宫正始》引录了《荆钗记》七十五支曲文,这七十五支曲文便来自两种不同的版本,一是元本,一是明改本。
这两种版本剧名有别,“古本《荆钗记》,不曰《荆钗》,直云《王十朋》”。[1] “元之《王十朋》,今之《荆钗》也”。[2]曲文也有异,如钮少雅云:“余未识原传时亦如之,后幸得睹元本,始知其全本词文皆与今改本《荆钗记》者大不同耳。”[3]

《荆钗记》现全本流存的皆为明代刊本,本编收录六种:
一是明嘉靖姑苏叶氏刻本,题作《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共二卷。
二是明万历刻本,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共二卷。
三是明万历金陵书林世德堂刻本,题作《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节义荆钗记》,共四卷。
四是明茂林叶氏刻本,题作《新刻王状元荆钗记》,共二卷。
五是明毛氏汲古阁刻本,题作《绣刻荆钗记定本》。
六是明万历刻本,题作《屠赤水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共二卷。
这六种刊本由于为不同书坊所刊刻,其间也有着差异。若按时代的先后及具体曲文、故事情节等的差异来划分,可将其分为两个系统:
姑苏叶氏刻本和茂林叶氏刻本为一个系统,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汲古阁本、屠赤水评本等四种为另一系统。
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不仅刊刻的年代有先后,即一为嘉靖,一为万历,而且两者之间有着承继关系,世德堂等刊本存在着在姑苏叶氏刻本和茂林叶氏刻本或与其同一系统的版本的基础上改动的痕迹,如《赴试》出,姑苏叶氏刻本和茂林叶氏刻本上场的脚色有生、末、净、丑四人,而世德堂本等刊本皆无丑脚出场,但最后一句下场诗却仍由丑念。显然,这是删改未尽,留此痕迹。

由于这两个系统的刊本产生的年代有先后,因此,两者在剧本形式、曲调格律和故事情节上,都有着差异。如在剧本的形式上,姑苏叶氏刻本和茂林叶氏刻本虽已分出,但无出目,而世德堂本等刊本不仅分出,而且有出目。
早期南戏的剧本因不是供人案头阅读的,是供演员演出所用,故全本戏虽有段落可分,但不分出,更无出目,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元本《琵琶记》、成化本《白兔记》等皆是,直至明代文人参与南戏创作与改编后,为方便阅读,才将全本分出,并加上出目。
姑苏叶氏刻本和茂林叶氏刻本虽已分出,但还能看出早期南戏古朴的剧本形式,而世德堂本等刊本的剧本形式则与明代文人所作的传奇剧本风格完全相同,即较为精致。
另外,在故事情节上,两者也有差异,最后王十朋与钱玉莲重会团圆的地点,姑苏叶氏刻本和茂林叶氏刻本皆作“舟中会”,写钱载和升任两广巡抚,坐船赴任途中,路过吉安府,时任吉安太守的王十朋前去拜谒,钱载和知道王十朋就是玉莲的丈夫后,便在船上设宴,邀王十朋及其母亲赴宴,使两人得以团圆。
故其第一出概括剧情大意的【沁园春】词云:“在楼船相会。”而世德堂本等刊本王十朋与钱玉莲重会的地点是吉安玄妙观,谓钱玉莲与王十朋皆以为对方已亡,上元节,到吉安玄妙观追荐亡夫(妻),不期而遇。
玉莲回府后,告知养父钱载和,钱载和便在府中设宴,邀王十朋赴宴,席间使十朋与玉莲团圆。故其第一出概括剧情大意的【沁园春】词则作“吉安会”。

从全剧情节的发展来看,各本的玄妙观相会不合情理,因为在两人于玄妙观相会之前,只是交代钱载和由温州太守升任福州安抚,从温州来到福州,并没有交代到吉安。后突然出现两人在吉安玄妙观相会及钱载和宴请王十朋的情节。
吉安与福州相去甚远,钱玉莲与钱载和怎么可能突然在吉安出现呢?这样的结局安排,显然与前面的情节不合。前人似也看到了这一结局的不合理,如李卓吾评本在【沁园春】词的“吉安会”三字上批曰:“原作舟中会为是。”
在现存的《荆钗记》中,除了有全本的形式流存外,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戏曲折子戏选集中,也大多选收了《荆钗记》的单出。

本编收录明清时期二十六种戏曲折子戏选集中的《荆钗记》散出、只曲:
选集名所收出目
《风月锦囊》:家门、会讲、庆诞、议亲、受钗、绣房、辞灵、合卺、分别、赴试、闺念、参相、获报、大逼、投江、哭鞋、见母、遣音、荐亡、责婢、团圆
《南北词广韵选》:合卺、亲叙、庆诞、遣音、晤婿、议亲、哭鞋、误讣
《吴歈萃雅》:寿宴、忆别、议亲、相别、送亲、限别、捞救、行路、议婚、苦别、节宴、严训、讲学、祭江
《词林一枝》:王十朋南北祭江
《徽池雅调》:承局送书、孙汝权假装卖花
《乐府菁华》:玉莲抱石投江、十朋母子相会
《乐府红珊》:钱玉莲姑媳思忆闻捷
《乐府珊珊集》:议婚、送亲、议亲、南北祭江、推拷梅香
《玉谷新簧》:十朋母子相会
《摘锦奇音》:十朋拜母问妻、十朋母子祭江
《南音三籁》:议亲、合卺、送亲、苦别、错音、行路、严训
《尧天乐》:钱玉莲绣房议婚、十朋母官亭遇雪
《时调青昆》:玉莲投江、十朋祭江
《词林逸响》:忆别、别任、苦别、捞救、祭江、行路、严训
《怡春锦》:送亲、祭江
《大明天下春》:玉莲别父于归、玉莲抱石投江、母子相会、十朋祭玉莲
《乐府万象新》:姑娘绣房议婚、继母逼莲改节、玉莲抱石投江
《万锦娇丽》:荆钗纳聘、绣房议亲、母子相逢、十朋祭江
《醉怡情》:哭鞋、见母、祭江、舟会
《歌林拾翠》:哭鞋忆媳、十朋见母、祭江奠妻、舟中相会
《赛征歌集》:拷问梅香
《玄雪谱》:见母
《千家合锦》:绣房议亲
《万家合锦》:十朋祭江
《审音鉴古录》:议亲、绣房、别祠、参相、见娘、男祭、上路、舟中
《缀白裘》:说亲、绣房、别祠、送亲、遣仆、迎亲、回门、参相、改书、别任、前拆、哭鞋、女祭、见娘、男祭、开眼、上路、男舟、舟会

在这些戏曲折子戏选集中,由于选收者在选收时所依据的底本不同,或在选收时也作了改动,因此,其中所选收的《荆钗记》也各有特色。
如《尧天乐》卷一下层选收了《十朋母官亭遇雪》一出,这出戏演十朋母赴京途中遇雪的情节,其中写当时的天气是“关河雪冻,四野云横”,一派严冬景象。可是在今存的明刊本中皆没有这一情节,而且十朋母亲赴京的时间是在春天,地点又是在南方,不可能遇到大雪。
又在各明刊本中,送十朋母赴京的是李成一人,而在《尧天乐》中除李成外,还有春香。如十朋母云:“成舅,老身受苦理之当然,你二人呵,受尽奔波,多多感承!”又【下山虎】曲云:“山程共水程,长亭又见家乡,愁杀春香、李成。”
显然,这出戏的情节是后人增加的。又如《徽池雅调》卷一上层选收了《孙汝权假装卖花》一出,演玉莲与婢女春香在花园内赏花,孙汝权从花园外路过,听见园内有女子说话声,便假装卖花,企图勾引玉莲,被玉莲斥退。这一情节不见于各明刊本。
另外,若按唱腔来划分,以上这些选集所选收的《荆钗记》单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昆山腔选本,如《吴歈萃雅》《词林逸响》《怡春锦》《醉怡情》《审音鉴古录》《缀白裘》等;一类是青阳腔选本,如《词林一枝》《徽池雅调》《玉谷新簧》《尧天乐》《时调青昆》等。昆山腔选本的曲文与明刊本虽也有一些出入,但曲调的句格字声等格律变化不大。

青阳腔选本在曲文中则加有滚唱和滚白,如《尧天乐》卷一下层《钱玉莲绣房议婚》《乐府万象新》前集卷四下层的《姑娘绣房议婚》出,在曲文中增加了许多滚唱和滚白。
《荆钗记》是昆曲中的经典剧目,本编也收录了《纳书楹曲谱》《荆钗记曲谱》《昆曲大全》《集成曲谱》等四种昆曲曲谱中的《荆钗记》曲文。
《荆钗记》是南戏的经典剧目,明清时期的曲律家们在编撰戏曲格律谱时,都在曲谱中征引了《荆钗记》的曲文,在宫调、平仄、句法、用韵、板式等曲调格律上为曲家作曲填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由于这些曲谱所征引的《荆钗记》曲文引自不同的版本,因此,这些曲文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故本编也辑录了《南词新谱》等六种曲谱中的《荆钗记》曲文。

前言
一、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
二、李卓吾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
三、世德堂本《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节义荆钗记》
四、茂林叶氏刻本《新刻王状元荆钗记》
五、汲古阁本《绣刻荆钗记定本》
六、屠赤水先生批评荆钗记
七、明清《荆钗记》选出
八、曲谱《荆钗记》选曲
注释:
[1]《南曲九宫正始》第四册【中吕过曲·漁家傲】曲下注,清顺治间刊本。
[2]《南曲九宫正始·凡例》,清顺治間刊本卷首。
[3]《南曲九宫正始》第四册【中吕过曲·漁家傲】曲下注。
配查网-配查网官网-正规的股票场外配资平台-辽宁股票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低息配资股票在落地前可分裂成多个弹头;因其速度极快
- 下一篇:没有了